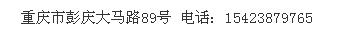
我看着他像疯子一样用手砸着铁窗,笑着对他说:
“你觉得我会生下一个魔鬼的孩子吗?”
我是被他拐来的女人,我以尊严和自由起誓,我永远不会爱上他。
1
余弃之认罪的唯一条件是见我一面。
他头发变短了,坐在铁窗前两手相互交握。
从我进来,他的目光便没有离开过我。
交握的双手在我坐下时变得繁忙,我从未见过这样紧张的余弃之。
说话时语气里都带着小心翼翼,“阿喜,你不要害怕,他们不会……”
“余弃之,你认罪吧。”
我打断了他的话,他被抓时,我们已然撕破了脸。
我不懂,他为何到这个时候还要自欺欺人。
对于我的直接,他并没有惊讶,他静静地看着我。
面上的神色变得复杂起来,笑容开始掺杂了苦涩。
他就带着这样的神色看着我,直到那双望着我的眼睛里渐渐聚起了一层薄雾。
然后,他笑着说:“阿喜,如今你竟连骗我一下都不愿意了吗?”
从前我幻想过无数次今天这个场景。
在余弃之伏法认罪的时候,在他即将被枪决的时候,在我大仇得报的时候。
我要用尽天下间最具侮辱性的词汇羞辱他,辱骂他。
我要把我心中对他所有的恨意全部化作语言来折辱他。
如今这一天终于到来了,我却发现,自己心里竟是这样平静,平静得像一个旁观者。
原来他也知道我一直在骗他,可是骗人也是需要力气的,我说:“我演累了。”
他终于不能再笑出来。
隔着铁窗,我看到他紧握的双手,手腕上的手铐链条绷得直直的。
那一刻,他应该是恨我的。
他说过,这世上我是他唯一牵挂的人,但这个人却背叛了他。
过了会,他的拳头松开了,手铐链条与大理石桌面碰触,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
他整个人靠进了椅背里,仿佛所有力气在刚才几秒钟里用完了。
他带着妥协后的疲惫说:“我只有一个条件。”
我看着他,他亦看着我,我等着他死前唯一的条件。
他说:“留下那个孩子。”
他说:“我只有这一个条件,阿喜,留下我们的孩子。”
口气里带着恳求。
我沉默着,他忽然朝前凑过来,双手穿过铁窗。
手指挣扎试图穿过铁窗,手铐链条与铁窗相撞,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他想握我的手,可惜戴着手铐,他碰不到我。
他几乎绝望地看着我。
我垂下眼睫,看着他那近在咫尺、与我隔着仅仅一指宽的手掌。
因为常年握枪,虎口上的茧子很厚。
他很可怜,可死在他手里的那些无辜的人更可怜。
我说:“余弃之,没有孩子了。”
我抬起头来看他,看他绝望着从椅子上站起来,看他疯子一样用手砸着铁窗。
我对着他笑,我说:“你觉得我会生下一个魔鬼的孩子吗?”
三年前的冬天,我被人卖到了缅甸。
一起被卖去的那一波人里死的死,残的残,只有一个我,还算完好.
代价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身体。
我曾像狗一样在余弃之跟前苟活,活得没有一点尊严。
发现自己被卖后,有个女孩子大哭大叫,然后被一帮拿着铁棍的壮汉打断了一条腿。
我因为上前阻止,左手被他们打伤,我们缩在角落里,又怕又疼。
红艳艳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衣服。
而那个时候余弃之就坐在我们跟前。
这个亡命之徒,穿着一身黑色西装,身姿挺拔得像一棵松树。
那张刀削般的面孔上,眉毛微微蹙起,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敲,那些打人的便住了手。
如果不是身边躺着两个几乎被打残了的女人,你决不会想到这个斯文的男人。
会是这里的老大。
他说:“对待女孩子何必这般粗鲁?”
打手说:“她不肯按着咱们说的办,还嚷着要报警。
来了几天了,就是一点不配合,还有这个女人竟然敢阻止……”
余弃之没有作声,他从椅子上站起来,走到女孩跟前。
他一弯腰,那女孩吓得一阵瑟缩。
余弃之说:“你要报警?”
女孩满脸的泪水,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。
余弃之看了眼我流血不止的手腕,他说:
“你知道吗,在这里帮人不一定会有好报。”
我不知道是因为疼还是因为害怕,上下牙齿磕在一起,咔咔作响。
那一刻除了恐惧还有钻心的疼痛。
他站起来,那帮走开的打手眼看着又围了过来。
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,忽然出声说道:“你们不要再打她了!”
本已走开的男人忽然停了下来,他回转过脸来,眼睛里带着疑惑看着发声的我。
我声音又软又弱,早没有了刚才的勇气。
“她会被打死的。”我哆哆嗦嗦地看着他说道:“别再打她了好不好。”
他的眼睛里燃起一丝兴趣,本来是要走,现在却完全站住了。
他带着一丝笑意,同我说道:“犯了错是要受罚的——除非你代她。”
见我犹豫,他讥讽一笑:“不敢了?”
那女孩满脸的泪水,腿上血流不止,再打下去非死不可。
我所有的勇气都在那一刻发挥出来,说出的话却是没有什么底气,我说:
“我代她。”
他仿佛很意外,在我脸上看了几秒,唇角若有若无的笑容渐渐敛去。
他朝着那些打手使了个眼色,那帮人朝我走来。
在我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,一根铁棍挥下,照着我本就受伤的手腕夯了下去。
疼痛让我忍不住尖叫,然而刚一出声,我便将它压了下去,我咬着唇死命望向那个男人。
而他,面无表情。
2
我的左手几乎废掉,连抬都抬不起来。
后来即便请了这地方最好的医生,也没能让它完全恢复过来。
那些日子,我与受伤的女孩相依为命。她帮我包扎手腕,我帮她治疗腿伤。
他们把我们关在潮湿的地下室里,男女同住,一个大通铺。
女生叫阿兰,只有21岁,连大学都还没有毕业。
只是出门旅了趟游,就被人卖到了这里。
没有人给我们找医生,我用木棍给阿兰把腿固定住。
没有药,我从看管我们的人那里讨了一些酒来给我们消毒。
阿兰伤得要比我重得多。
我曾医院医治,结果那帮壮汉看着我哈哈大笑。
好像我讲了一个笑话。
那之后,我便知道,他们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人,是死是活他们也根本不在乎。
我和阿兰都没有死,阿兰腿瘸了,而我的左手也等同于废掉,以后再也不能拿重物。
3
两个月之后,我又看到余弃之,这一次他穿的不再是西装,而是一身干练的迷彩服。
看到阿兰时,他“咦”了一声,说道:“你竟然没有死。”
在他口中人命仿佛如同儿戏。
阿兰很怕他,抖着身体说:“是不喜姐姐帮我治好的。”
余弃之的目光落到我身上,有点疑惑,还有点自嘲,他说:“你叫不喜?”
我很怕他,他那目光投来时,我忍不住想要后退。
“窦不喜。”我小声回他。
他听后,忽然笑起来,口中念道:“窦不喜……”
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,所以听后只觉得毛骨悚然。
身体紧紧贴在墙边,生怕自己哪句答错惹到他。
我当然是想错了他。
他只是从我的名字里想到了自己。
后来我总想,大约就是因为我这个名字,才让我得了一块免死金牌。
因为在那个晚上,余弃之的仇家忽然杀了过来。
余弃之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,枪林弹雨之中,我们被人从地下室里撵出来逃亡。
那一次死了很多人,和我们一起被拐来的人里只余下我跟阿兰。
余弃之他们是打算放弃我们的,在一片树林之中,我抱住了余弃之的双腿。
仰着糊满泪水的脸庞求他。
“求求你带我们走,求求你。”
他垂着头,在我脸上看了片刻,最后拉起我的胳膊,把我拖进了汽车里。
我拉着阿兰的手,恳求地看着他,他忽然就笑了。
握着手枪在鬓角上轻轻一磕,笑说道:“你以为你是谁?”
但他最终还是把阿兰拉了上来。
4
那一次余弃之受了伤,一颗子弹打在他的胸前,只要再偏一点,他的命就保不住了。
我们在一个村庄里安顿下来,村里条件简陋,跟随他的医生也在枪战中死去了。
或许是因为我曾救活了重伤的阿兰。
他们找上了我,拉着我一定要让我给昏迷的余弃之手术。
我不肯,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医生,手术是万万不行的,但他们不听。
最后我被他们用枪指着站在了“手术台”上。
左右是死,我决定晚死一会,于是大着胆子把余弃之胸前的那颗子弹取了出来。
或许是我够幸运,反正余弃之没有被我治死。
子弹取出的那一瞬间,余弃之因为疼痛曾有短暂的清醒。
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,他脸上仍是云淡风轻,那种看淡生死的心态。
哪怕他是十恶不赦的大恶人,依然让我心生敬畏。
他说:“竟然是你。”
话毕人就昏迷过去了。
5
因为这台“手术”,我变成余弃之的救命恩人。
可惜这个恩人待遇并不好,不光不好,还要负责照顾余弃之。
不只照顾他,我和阿兰还要负责给这些人做饭。
做饭我并不觉得怎样,我最怕的是那些许久没有见过女人的男人。
他们的目光像许久没有吃过肉的狼,躲在角落里,看着我跟阿兰咽口水。
有一次煮饭时,一个年轻的男人忽然跑上来从后面抱住了我,拖着我就往角落里走。
最后是我摸到了他别在腰里的枪,照着他的脚上开了一枪,才算逃过一劫。
男人疼得嗷嗷嗷叫,枪声引来他的朋友,他们拿枪指着我要为朋友报仇。
“谁敢?”我举着枪努力让自己镇定,不想却引得那帮人一阵嗤笑。
“我是你们老大的女人,如果不怕他杀了你们,那就尽管过来!”
或许是这句话吓到了他们,他们没有敢再上前。
面面相觑了半晌,最后从厨房里退了出去。
6
最终这件事还是惊动了余弃之。
那天我给余弃之喂药的时候,他忽然抓住了我的手腕。
我吓了一跳,手里的杯子落在地上。
我的手还被他抓在手里,我看到自己的腕上曾经留下的伤口。
当时因为伤口处理得不好,旧伤又发了炎。
我不敢往回抽自己的手,只是任他握着。
他抬起眼睑,卷翘的睫毛又浓又密,他说:
“你什么时候变成我的女人的?”
我猛地抬起眼眸,惊慌失措地看着他,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这个问题。
他却忽然笑了,朝讽道:“怕我?”
我不作声,他勾起唇角,声音竟是难得温和,他说:
“抱着我的双腿让我救你的时候,你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”
我抬起眼皮看他,他眼睛里带着一丝戏谑:“窦不喜,你的命是我的。”
可如果没有你,我也决不会来到这里,你是我所有不幸的根源。
但这些我不敢说。
我对他露齿一笑,把心里所有的想法隐去。
7
那个曾经搂抱过我的男人死了,死在余弃之住的那间房子。
余弃之手中的枪还没有收起,看着我筛糠一样的身体,他说:“过来。”
他拉住我的手,指着地上死人,说:
“窦不喜,以后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。”
我忍着胸腔里的恶心,想对着他笑一笑。
可脸僵硬得不像自己的,扯出的笑容也许比哭还要难看。
那天之后我不再负责给别人做饭,我只需要照顾余弃之一个人。
阿兰也有了帮手。
当然也不会再有人来骚扰我们。
阿兰问我,我们还能不能回家。
问这句话的这天是中秋节,我们坐在小院里。
看着头顶圆圆的月亮,这本是一家团圆的日子。
可是我们却躲在异乡,随时有着生命危险。
阿兰是个幸福的孩子,有爱她的爸爸妈妈,有喜欢她的弟弟。
所以这个日子对她来说是痛苦的。
但我并不,我的家庭并不幸福,母亲怀我时父亲出轨。
如果不是月份太大,母亲是打算把我打掉的,我的到来是不受欢迎的。
就连我的爷爷奶奶也因为重男轻女并不喜欢我。
母亲常常调侃,说我是个没人喜欢的女孩子,这样调侃着就把我的名字定了下来。
没有人在乎我叫什么,就连我自己慢慢地也对此变得麻木。
小时候有同学嘲笑我,说我是个没人喜欢的孩子,我哭着回去问母亲。
而我母亲竟指着我哈哈大笑,她说:“你本来就是没有人喜欢的呀。”
幼小的我站在风口里,脸上落满了泪水。
邻居看不过去,拉着我的手,她说:
“谁说的,我家阿风就很喜欢不喜。”
然后拉过自己放学回家的儿子,笑问道:“是不是阿风。”
我期待地看着那男孩,大有他不点头我就继续哭的架势。
最后那男孩对着我点了点头。
我流着眼泪咧着嘴冲着他笑,他忽然就对着我弯了弯唇角。
然后把一块糖塞进我的手里,他说:“吃了糖,就不哭了,好不好?”
8
那天夜里我已经歇下了,余弃之忽然又让人把我叫了过去。
他的房里没有开灯,只有餐桌上摆了两根蜡烛。
我看到桌面上摆了几盘菜,其中一盘里放的是糖果,我捏了一颗。
拨开糖纸,放进嘴里,入口是一股榴莲的味道。
“好吃吗?”
我猛地转身,余弃之站在门前。
他已大好,有时一整天都不在房里。
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,站在那里又有多久。
他腕上戴了块手表,低头看了看,说道:
“再有十分钟,中秋就过去了。”
他走过来坐在餐桌前,见我站着,抬起头来问我:“不坐吗?”
我没有坐,而是问他:“你找我有事吗?”
借着微弱的烛光,我看到他微微蹙起的眉头,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言。
我竟用这种口气同一个亡命之徒说话。
他倒没有同我计较,朝我伸出来手来:“过来。”
我手搭过去,他的手有些潮热,握着我的手将我拉进他的怀里。
然后把我按在他的腿上,他目光投在我的脸上,而我却垂着头不敢直视他。
离得太近,近到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声,鼻息间的气息扰得我的脖子很痒。
可我却没有勇气推开他。
他解开我脖子里衬衣的纽扣,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打着冷战。
他轻抚着我脖颈里的皮肤,轻笑着说道:
“窦不喜,你在发抖,是因为不喜欢我碰你吗?”
面对他的询问,我竟连说一句实话都不敢讲,轻摇了摇头,说:“不是。”
在这个不太平的地方,我还需要他的保护。
哪怕我恨他,厌他,我仍然不得不服从他。
而他不过把我当成一件玩物,想起来逗一逗,想不起来便把我扔到一边。
9
我和阿兰第一次准备逃走,是在余弃之进行交易的那天晚上。
或许是因为这场交易的重要性,也或许他对我和阿兰有了一定的信任。
总之那个晚上他几乎调走了身边所有人,我们所在的院子里。
只余了一个看管我们的男人。
那个男人还是个嗜酒如命的人,我在余弃之那里偷了一瓶白酒就把他收买了。
然而我们的逃跑没有开始就失败了。
阿兰腿上有疾,没出村子就疼得走不动了。
她说:“不喜姐,你走吧,不要管我了。”
在那种时候,人是不能思考的,出于本能,我转身离开了。
走出好远,看到阿兰在月光下,流泪看着我。
那个时候我就在想,无论如何,我以后是要把她救出来的。
我是在一座破庙前被余弃之抓住的。
庙里只有一个僧人,被余弃之用枪指着。
他笑看着我,意有所指地说道:
“窦不喜,你是要逃走,还是准备来见什么人的?”
他身边围了四五个男人,个个拿着枪。
我知道,只要我答错一个字,身上就会被打成筛子。
我用惊恐的目光看着他,泪水在眼睛里打着转,声音颤抖着同他说道:
“我没有想过逃走,我是来求平安符的,你受了伤,我……”
他坐在那里看着我,手里把玩着手枪,目光冷冷淡淡,唇角却挂了一丝微笑。
我的声音在他清冷的目光里渐渐小下去,我咬着唇,胆怯地看着他。
很显然,他并不相信我的话。
求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,我垂下眼睫,心死一般地说道:
“你若不信,杀了我就是了。”
但他却忽然开口,说道:“符呢?”
我抬起头来,他笑看着我,说:“不是来求平安符的吗?”
我慌慌张张地从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平安符,但我不敢靠近他,站得远远的。
他说:“拿过来。”
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,没到跟前就被他捉住手腕拽进了怀里。
他捏住我的下巴,在我耳边轻声说道:“窦不喜,你最好没有撒谎。”
他手上的力气很大,我的骨头像是被他捏碎了一般。
疼痛让我眼睛里蓄满泪水,但我却不敢呼疼,就这样带着满目的水光朝他扯出一个笑容。
他盯着我的眼睛,忽然将我从他跟前推了出去,举起手来“砰砰”朝前开了两枪。
我大惊之下,转头看去,发现一个男人倒在了地上。
死的正是今晚看管我们的人,他的脸上还挂着懵懂的表情。
大约从未想到,余弃之会忽然朝他开枪。
下一个死的会是谁呢?我转头看向那个跪在地上的僧人。
我被余弃之从地上拎了起来,他像没事人一般,握着我的腰肢,轻声说道:
“窦不喜,你怕什么,死的又不是你。”
我把脸埋进他的胸膛,上下牙齿嗑得直响,我说:
“余先生,我有些害怕,今晚上不杀人了好不好?”
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僧人,然后盯着我的眼睛,笑了笑,竟然答应了,说:
“那就听你的,不杀了。”
10
余弃之曾说过,一个人如果犯了错,在他这里是会受到惩罚的。
说起来好笑,这话竟出自一个大恶之人。
他对我的惩罚很快就到来了。
他带我去参加一个“生意”伙伴的宴会。
在那场宴会上,他把我送给了他的生意伙伴。
我是以余弃之女伴的身份去的,但对方的目光却一直在我身上打转。
余弃之并不是一个大方的人,他一向是睚眦必报。
我在他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,他始终不相信那一晚上我是为他求符的。
所以当对方笑着把目光投到我的身上,并欣赏地同他说道:
“余先生今日的女伴有些与众不同。”
余弃之也只是低头朝我看了两眼,然后淡淡说道:“你若喜欢,送你就是了。”
我大惊之下,几乎忘记了掩饰自己的表情,我仰起头带着恳求的目光看着他。
但他的目光却是清冷的,他垂着眼睫,轻笑着同我说:
“能让仇先生看上,是你的荣幸。”
我知道求他没有意义,在他这里,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,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
而我也不过是他众多女人里的一个,他没有理由为我搞特殊。
在我怔愣的片刻里,他已垂着眉眼同我说道:“还不到仇先生跟前去?”
我是个怕死的人,也从来没有把余弃之当成一个有道德感的正常人。
我放弃了对他的求助,朝他露出淡淡一笑。
从他跟前的沙发里站起来,走到对面姓仇的身边。
当姓仇的男人伸手搂在我腰上的时候,我看到余弃之略略冷淡的眼眸。
而我却垂下了眼睛。
那天晚上,我是跟着姓仇的男人离开的。
后续精彩内容提前看:
车还没有开到他的家中,就被人用车截停了。
汽车横在马路中间,车里的余弃之大步走来,拉开车门,冷冷地说道:“下车。”